那是1991年4月份的事。当时的《读者文摘》(现名《读者》)正举办"十年征文"活动,首次刊登的3篇征文作品中有一篇题为《我的财富》的文章,作者是青海乐都县的一名普通女性,名叫王国玫。文末注有作者的详细通信地址。
从这篇质朴无华的作品中,我读出了她的才气与优秀,尤其是文中的"我",远道购书风尘仆仆的形象,一如我梦想中的女孩。说来奇怪,一向不爱与人通信的我,竟鬼使神差地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读过你的作品,我有一种预感,你将作为我的伴侣,分享我人生的苦难……"心高气傲的我发出这封霸气十足的信后,突然间又后悔自己一时的冲动:未免太冒昧太荒唐了吧--要是人家是有夫之妇,要是人家男儿身女儿名文章也是糊弄人,那该怎么办?我心下一急,忙奔往邮局打算取出那信,不料迟了一步,邮局已经关门。
很久之后,我居然收到了一封寄自青海的来信。娟秀的字体令我抨然心动,特别是精心折叠的信笺,恰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鸟。信中她不无讥诮地问我:"……为了创作,我已荒废了学业,你能忍心因为其他,让我荒废更多吗?"我不由一阵心悸:天哪!才是一位高三学生!我只好克制自己对她的迷恋,简单地写了一封祝她考上大学的信。
其实,当时的她每天都能收到读者来信数十封。为不冷落热心的读者,她白天上学,晚上读信复信,几个月里邮资就花了好几百元。父亲特别节俭,骂她乱花钱;严厉的老师责备她不上进;好奇的同学们羡慕她朋友遍天下……结果呢?她以15分之差名落孙山。
这可闯了大祸。一直将她当"秀才"而且在人前吹嘘她一定能考上大学的爷爷在考分公布的第二天竟给气死了。于是,她像罪人似的长跪在爷爷的棺木前,哭成了一个泪人。
爷爷出殡后的第二天,四面楚歌的她收到了我写给她的第三封信。在第一封信中我称她为"王国玫君",加上了一个君字;第二封信我称她为"国玫君",减了一个王姓;这第三封信依次递减理所当然成了"玫君"。也许是这个称谓对她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震撼力,她终于向我敞开了少女的心扉。她在信中告诉我:"因为我的那篇文章,全国各地读者来信逾千封,多数是男孩写来的,其中不少欲'图谋不轨',却又遮遮掩掩,能像你这样直奔主题的,实在绝无仅有。而且,你是惟一没有向我索求照片的求爱者。看来,你很相信自己的感觉,以为我并不丑陋。"我也去信告诉她:"是的,我确信你是一位不媚俗的漂亮女子。但是,在你我未曾谋面之前,我不希望将你拘泥于一张照片中,以此凝固我的想象。"我是一个赌性很强的人,说到做到,后来一直到结婚,我没有得到她的一张照片。从这点上,我也看出了她是一位很自信很特别的女孩。
但在中秋节前夕,我主动给她寄去了一张照片和一盒歌带。在题字"去向何方"的照片中,目视前方的我站在一排紧闭的大门前,脚边放着一个旅行袋,看上去就像一个远行后尚未找到归宿的人。歌带上录有一首我清唱的歌--《我想有个家》。后来听她说,接到这份礼物时,正是中秋节,更巧又是她的生日。这意外的惊喜使她相信爱的天空有神的指引和安排。那天,她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面听着《我想有个家》的歌声,一面看着题照"去向何方"中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终于泪流满面。其实她也知道,这张照片是我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
生日中的她为我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等你,等到花开花落,等到月缺月圆,等到形容憔悴,等到梦想成真!我相信你会来,也许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也许在一个日落西山的黄昏……"
一段时间里,这种离奇的恋爱受到双方身边不少人的嘲弄和嗤笑,尤其是她父母,竭力反对这桩婚事,但最终拗不过她。我们已经相约了一个见面的日子。
当时,长沙--兰州的航班刚开通,在长沙工作的同学决定为我购买一张机票。于是,我将抵达兰州的时间告诉了她。谁知道后来机票没买上,而坐火车怎么也赶不上约定的时间,结果让她苦等了一整天,陪伴她的同学气得大骂:"准是个骗子!"同学走了,她固执地等着!
在西行的列车上,心急火燎的我坐立不安。临近乐都,我的心更为忐忑。毕竟,我不能完全摆脱世俗的考虑:我的贫穷与寒碜是否经得起她家人的审视?除此之外,我更担忧的是,一旦见面,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会不会各自露出大失所望的神态?总之,这段恋情,会不会像青春岁月里的许多梦,以浪漫开始,而最终却无一例外地幻灭呢?
黄昏,在我们相约的站牌下,我一眼看见有位穿黄风衣的女孩正义无反顾地向我走来。一定是她!难以相信,她果真如我梦中一样的美丽,像她的文章一样质朴。
"你,才来!"她望着我,眼中亮着晶莹的泪花。
我好感动。在此之前,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地相爱了许久,却未曾谋面,想不到竟然一见如故。我一把握紧她的手,干言万语哽咽在喉头……
一个星期后,我带她回湖南,随行的还有她父亲。
在我供职的那所学校里,她父亲环视着不足20平方米的小住房以及室内简陋的陈设,脸上露出了鄙夷和不悦。晚上,他单独对女儿说:"你全看见了,啥都没有,与他过日子不容易。明天跟我回吧。"她毫不犹豫地说:"爸爸,你和妈妈当初不也是白手起家的吗?请相信我们吧!"父亲无言以对。
这年冬天一个很平常的日子里,我和她在一位朋友的茶座里举行了简单而别致的婚礼--拼上几张条桌,摆上一些水果点心,来宾人手一杯葡萄酒,祝辞过后,大家像沙龙聚会一样尽兴地聊了一个通宵。
婚后,我离开学校,与她开办了一家书屋。
次年10月,一个小精灵伴着初升的太阳呱呱坠地。我们给这个缘于一篇征文的儿子取名文心。
正当我们沉浸在小家庭的欢乐中时,灾难却不期而至。那天,我送一位朋友去火车站,归途中淋了一场暴雨。当天下午,我开始发高烧,继之肚子疼痛难忍,并伴有呕吐现象。早年,我因突发性肠梗阻动过一次手术。莫非这次是旧病复发?经医院检查,果真!
经过一个星期的保守治疗,病情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更加严重。撕心裂肺的疼痛,一阵阵的呕吐几次使我昏迷过去。最终;我被送上了手术台。剖开腹腔,肠子已经广泛粘连,面对这一团乱麻,医生无从下手……4个小时后,从外地赶来的专家和主刀医生通过会诊,最终无奈地缝合了刀口,手术失败。
因肠粘连而导致的肠梗阻如果不予解除,意味着病人从此不能排解大便,其后果可想而知。哭干了眼泪的妻子最后选择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长期输液,延缓我的生命!
我在昏迷中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冥冥中,突然从地狱中醒来的我,看见爱人一手搂着儿子,一手为我按摩腹部。激动之下,我全身痉挛,大肠剧痛,随之是一阵痛快淋漓的狂泻。"通了!"我嘶哑地叫道。妻子一见这情景,顾不上收拾我屁股下的脏床单,扑过来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痛痛快快地流了个够。
一位料定我必死无疑的医生不相信这个奇迹,事后解释道:有可能是他爱人几天几夜坚持不懈的腹部按摩起了作用。我想也是这道理。
俗话说一病百病。极度虚弱的我虽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失去了免疫力,几乎同时染上了肠结核和心包积液。治疗心包积液必须用激素药,而激素药会导致结核扩散。无奈之下,医生不得不使用激素药,否则,心包积液会导致病人膏盲。心包积液治好后,扩散的结核杆菌侵入了我的五脏六腑和每一寸肌肤,腹膜结核、骨结核、淋巴结核……各种结核记满了我的病历。随之,大量抗痨药致使肝肾中毒。各种强制治疗一天到晚折磨着我,腹腔抽液,骨髓穿刺,石膏定位……我开始颓废消沉。
书屋距医院不过几十米,王国玫一会儿跑书屋,一会儿跑医院;喂过孩子又喂我,忙得团团转。夜深人静时,她强睁着眼皮给我这位睡昏了头的病人读一些振作人心的小文章。
每当我问起医疗费时,她总是轻描淡写地说:"你别急,还能对付。"
那时候我哪里知道,为凑每日将近200元的医疗费,她已经借遍了所有能借的亲戚朋友,最后不得不向他父亲伸手。第一封电报拍过去,没有回音,第二次第三次都没回音。她终于死心,发誓不再回青海。不料一个月后,一笔两万元的汇款寄了过来,附言栏内有八个字:早日康复,发愤图强!捧着这张汇款单,她突然理解了葛朗台一样悭吝的父亲的一片苦心。
后来我才知道,住院期间,在我妻子四处奔波八方呼援的感召下,人间温暖纷至沓来,演义出无数动人心弦的故事,足以影响我的一生,并为我后来的创作奠定了一种激昂的基调。
可当时,病榻上的我对此浑然不知。当爱人为筹款将书屋变卖后,我万念俱灰,待病情稍有好转,就执意回到乡下老家,栖居在几乎与世隔绝的一间土坯房子里。妻子拗不过我的犟脾气,只得随我。在这间潮湿昏暗的房子里我们一住就是两个春秋。
每天,她像服侍坐月子的女人一样服侍我,还得上医院请护士为我输液。哄睡儿子安顿好我后,她又忙里偷闲地走向村头庄稼地,拾一捆烧柴,拣一把青菜……曾经浪漫如诗的她变成了一位忍辱负重不露声色的强女人。她不再落泪,不再诉苦。看着她进进出出忙碌不停的身影,我感觉她就像一位忠实的女仆。
我的心开始悄然流血--"我有一种预感,你将作为我的伴侣,分享我人生的苦难!"那最初的情书就像一条通栏标题定格在我的眼前。可是,老天无眼,这哪儿是"分享",分明是她独自承担。一个弱女子的双肩何以承载我诸多的山一般沉重的苦难?!我决定狠心撵走她!
怀着放飞一只小鸟的悲壮,我开始在她面前怨这怨那,甚至动不动就摔碗。开始,她一忍再忍,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低头无语,尽量遂我心愿。菜淡了,忙加盐;咸了,又重炒……可是,我的挑剔越来越频繁,我的言语越来越蛮横无理。忍无可忍的她终于与我顶撞起来:"婆婆妈妈的,像个男人吗?"我说口而出地吼道:"你重新找男人去!你滚,给我滚!"她惊讶地望着我,然后扭头冲进房里,关上门悄悄地哭。哭够之后,她又没事似的走出来,行使她"仆人"的职责。
这样反反复复数次后,她终于悄悄地离开了我。那是一个细雨霏霏的早晨,她像平常一样,照例给我端上一碗鸡汤,照例将房子收拾整洁……不同的是,忙完家务,她不知从哪儿掏出一盒巧克力送给儿子,说:"文心,妈妈上街去了,你陪爸爸好好玩。"然后骑上单车走了。平常,她也是这时候上街买菜或者请医生去的,所以我没在意。
可这天,她没有及时回来。我知道她走了。晚上,儿子哭着找我要妈妈,我只得拥着儿子哄他:"妈妈打工去了,很久很久才会回来。"不懂事的儿子在我怀中哭着嚷着睡着了,梦中还在一个劲儿地叫妈妈。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百感交集。回味与她相恋相爱的每一个日子,我肝肠寸断。这场浪漫的婚姻就此了结了吗?原想,让她远离我的灾难会使愧疚的我轻松一些;却不料,她果真离去之后,我悲怆的心也随之被她携走,不知飘零何处。
连续几个晚上彻夜不眠,使我日渐好转的病情又加重了。我忍受不了这种夜不能寐牵肠挂肚的折磨,开始派人打听她的下落,青海、广州,所有能联系的地方都联系了,没有她的消息。试想,如果你挚爱的妻子突然失踪,你会是什么感觉?我知道,当时的我,痴痴呆呆的,几乎要疯了。几位好友见我这样,便筹集了一笔钱,决定分头寻找。
正在这节骨眼上,她从长沙打来电话。我在公用电话亭听到话筒中她问候我的声音时,竞当众泣不成声:"你快回来吧……"已在服装厂上班的她答应了我的恳求。
她要回来的消息儿子并不知道。可我一直觉得奇怪的是,好久不向我要妈妈似乎彻底忘记妈妈的儿子,这天早上正在凳子上摆火柴棍玩,摆着摆着,他突然站起身子,嘴里叫道:"妈妈!妈妈!"然后就像小狗一样钻出门外,往街道的方向奔去,跑了一里多路,年迈的爷爷才将他追回来。
傍晚,爱人到家后,听说这事,搂紧儿子忍不住哭道:"儿子,你是妈妈心头上的肉……"原来,当时正好是妻从长沙启程回家的那一刻。
深夜,等儿子睡着后,我一把抓紧她的手,袒露了我撵走她的真实心迹。她恍若梦醒,一头扎进我怀中……
后来,在她精心的护理下,经过长时间的治疗,我彻底病愈,重新开始文学创作。
以后3年,在债务如山的日子里,我和她始终患难与共,风雨同舟,一步步走出了困境。
回首往事,我不得不感谢那本《读者文摘》。如果没有她的倾心相爱,我就走不出那场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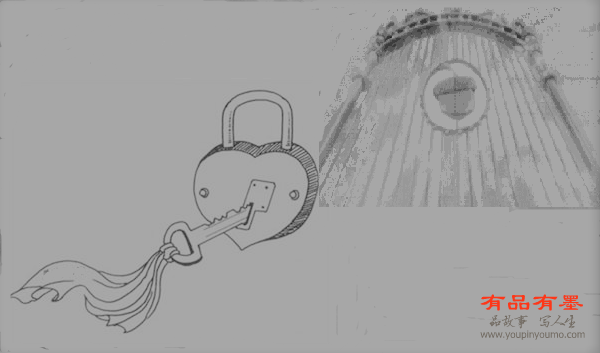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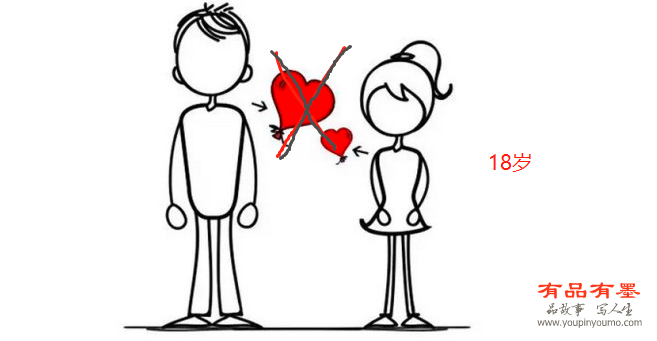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