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大学时,吉它正热,我一进校就知道全校有两个最知名的人物,一个是外语系的女生,因为天生不可思议的漂亮,被公认为"校花";还有一个就是林学系的男生,叫成波,很高很帅,留一头潇洒的长发,他的吉它弹得行云流水,听他弹琴,看着他缤纷复杂的指法,让人疑心这手指是仙人的手。
入校不久的迎新晚会上,我和成波认识了。很偶然却又像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份。当时我的演出正好结束,他的古典吉它奏排在后面,见我抱着手风琴回到后台,就让我用键盘给他的吉它正音,他说:
"你的手风琴拉得挺好。"
"谢谢夸奖。"我说。
"学了多长时间?"他问。
"接触挺早,进高中后我的成绩很差,家里打算让我考艺术学校,他们觉得我还有点音乐的天分,就请了老师教我,正经学了不到一年。"很自然的,我把这些告诉了他。
"怎么不继续学下去,却考到这儿来了,真可惜!"我明白他的意思,这个学校在大学只能算个末流,并不如人所愿。
"我也没想到。高二分到文科后,我的成绩又好起来了,于是就放弃了学音乐。当时觉得还是考个正式学校好,只想把音乐当作业余爱好。"
"有些人是为音乐而生的,不知道你是不是。"他的神情有些忧郁,不知是在感叹我,还是在感叹他自己。
我开始学吉它了。音乐都是相通的,有了手风琴的基础,我学起吉它来进步很快。何况我有一位难得的好老师--成波。
我学得很勤奋,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坐在床边对着《卡尔卡西教程》练指法,直到第二遍上课铃响,才慌慌忙忙地奔跑到教室。除了上课,我的业余时间都是怀抱着吉它度过的。在有些不大有意思的课上,我不是抄借来的曲谱,就是拿着背面划了六条线的铁铅笔盒练左手的和弦。手指上的茧子起一层,磨一层,别人看了我的手指头后惊讶得不敢相信这会是女孩子的手。那段时间我痴迷吉它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直到有一天同寝室一个同学正儿八经提醒我:"吴荞你知不知道,上一级物理系有个男生就是因为学吉它,一学期弄了四门补考,今年上不成学了。"一语惊醒梦中人,我稍稍有所收敛,上课也开始记点笔记,然而吉它带给我的乐趣,终是枯燥的功课所无法比的。
成波对我琴技的进步总是毫不吝啬给予褒奖,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你的音乐悟性真好,我真担心这样下去你会把我的东西学完,到那时我就得叫你老师了。"
然而只有一年,一年时间,还没等到我把他的东西学完,他就毕业回到故乡的小城了。他离校的前一天晚上,好几个琴友一起来到足球场空旷的草坪上,夏夜里月光温柔如水,清悠悠地泻在我们身上,怀中的六弦琴也镀上了一层银光,我们一起合奏《绿袖子》和《红河谷》,这些忧伤的旋律让人心中溢满了别离的感伤。我在幽暗中看着成波,他的长发遮住了脸,无法看清他的表情。也许他感觉到我在看他,抬起头来,凝视着我。我突然有些害怕这种氛围--这种膜胧的夜色和这种蒙的心情。我匆忙避开了他的眼睛,却听见他叫我的名字。
"轮指学会了吗?"他问我
"感觉还行。"我用轮指奏了一个和弦。
"你终于把我的看家本领也学去了,"他笑着说,"不过能教到你这样的学生是我的幸运。以后好好练,不要荒了。"
成波走后,吉它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知道,在一个小城里,有一个忧郁的男孩也在时时刻刻拥抱吉它,我们会在同一时刻奏响同一个和弦吗?暗夜里弹琴,是我们惟一的联系方式,我们期待着碰撞在天宇之间的和音共鸣。
他毕业后我继续在大学过了三年,我们没再见过。几年里我与两个朋友曾在学校旁边的"红豆"咖啡里办过几次吉它培训班,并没有发现很有灵气的学生,我也没有成为成波那样的好老师。
如今九年过去了,大学校园的情怀早已离我远去。我从一个城市奔波到另一个城市,不变的家当就是一把吉它,我不清楚我的内心深处是不是有些怀旧,或者说怀抱吉它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我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怀抱六弦琴坐在月光下,在手指的拨弄中慢慢回忆起年少时的激情与欢乐,忧伤和思念。
我到的城市越来越大,可一席安静的月夜之地却越来越难寻找。上大学时熬夜费神誉抄的满满一本曲谱,也在西安的一家小面馆里被人连包偷走了。那种伤心我不想再提起,我想到了多年以前坐在桌边凝望着我抄曲谱的成波。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还弹琴吗?还有我的那些因琴而结识的朋友们,在暗夜中,他们的琴声会不会不再悠扬,五线谱早已在风中飘散?
现在我住的地方,是一间小房子带一个大仓库,仓库空荡荡的,回声效果却出奇的好,这一发现让我伫立在空旷的大仓库中央感慨不已。我就常常这样在生存空间和音乐空间的尴尬交错中,缅怀旧日时光,为心灵找寻栖居的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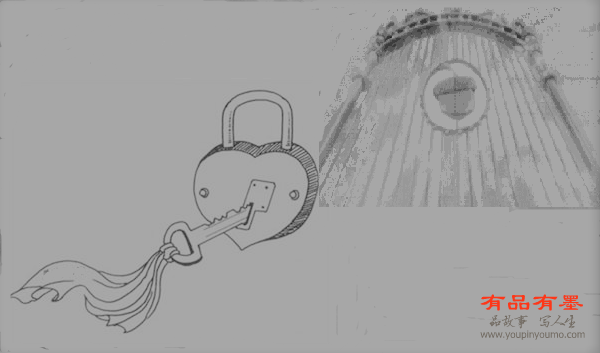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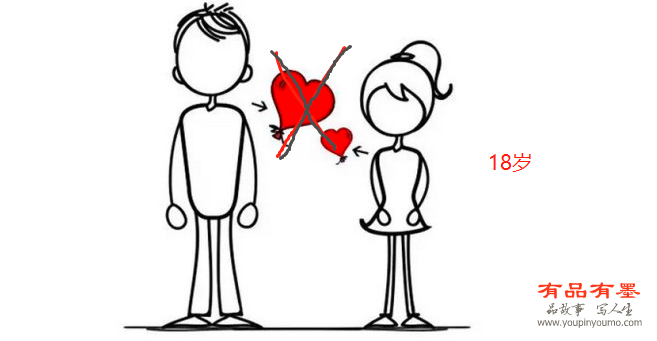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